
放在正文之前的後記:讀者留言告之,星期六貼文時的圖片,誤將張敬龍的圖片當成Alan Mak,已更正,並為此烏龍致歉。Mea culpa!
英國大選完畢,看似塵埃落定,但是留下兩個有趣的問題--其一是為何大批傳媒,會給予選上議員的華裔保守黨候選人Alan Mak(上圖,前排中)「麥大粒」這個名字,連他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,也要澄清「我沒有中文名字」。當我看到有關報道時,心裡浮現的第一個疑問,是為甚麼名字會那麼醜,第二個疑問是,如果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,那麼誤會的源頭是甚麼呢?
正因為此,在網絡做了一點調查,見到台灣的風傳媒,引述前引的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說,「麥大粒」這個名字是多間香港傳媒使用的,再順瓜摸藤一下,見到台灣批踢踢的鄉民訕笑香港的傳媒,也就不奇怪了。不過小弟好歹也對傳媒這行有點認識,認為此地傳媒不會貿然將一個只有華文譯音姓氏,加一個外語名字組成的姓名譯成麥大粒的,慣常的做法是叫他到「麥艾倫」之類,還要加上「音譯」的附注,以告訴讀者觀眾他們不能確定他的華文名字。
當然這可能有例外,前提是本地傳媒撰寫有關報道的人士,曾經親口問過Alan Mak本人有沒有中文名字,又或者看到其他傳媒,以一個很確定的語氣指明Alan Mak就是麥大粒。Alan Mak進入本地傳媒視野,是近數天的事,好像是「畸寶台」及「現在台」,以及方向報系兩份圾章,都是在五月六日才對華人參選今次英國大選的情況作出報道,並不約而同地都提到麥大粒,綜觀畸寶台的報道及現在台的報道,都直接將Alan Mak叫成麥大粒了--看來這個譯名的由來,像是第二個原因多點。
於是求助於新聞數據庫,看看有沒有頭緒,給我發現台灣的《聯合報》在五月六日,也有英國華人參加今次大選的報道--而在五月六日之前,無論是中國、台灣及香港的傳媒(以資料庫所涵蓋的範圍計),都未有提及過「麥大粒」的名字。找回當日《聯合報》的報道,也是斬釘截鐵的說Alan Mak是麥大粒,但嚴格點說,這不是《聯合報》的原創報道,而是轉載同一報系、在美國發行的《世界日報》的文章,再看看《世界日報》的報道,這次可找對了,因為這是蕭姓記者親自採訪、拍攝的報道,還要是在五月四日發稿、五月五日於世界日報見刊的。
「調查」到此,Alan Mak變成麥大粒的過程,很可能是這樣的:
五月四日-五日:《世界日報》記者訪問完Alan Mak後發稿,將這名字叫成「麥大粒」;
五月六日:屬同一報系的《聯合報》轉載文章;
五月六日:香港的電子傳媒發現有關報道,報道華人參選情況時,也稱呼Alan Mak為麥大粒;
五月五日-六日:方向報系可能因與聯合報系有合作關係,早在五月五日已收到《世界日報》稿件,而在五月六日有相關報道;
五月七日-八日:Alan Mak當選議員後,兩岸三地傳媒當然關心華人參選情況(難聽點說,是愛攀關係),而Alan Mak也發現有個奇怪的中文名時,就要特地澄清沒有中文名字了。
不知道《世界日報》的記者訪問Alan Mak時,是否有向他本人求證有沒有中文名字,但是隨後的事情發展,就顯示了傳媒其中一個做法,就是見到同行「很像」查證、確定了一個英籍華人的中文名字後,就照用如儀,其他跟風的媒體也照用不誤,但當源頭是一個美麗的誤會的話,就會出現其他人一致錯下去的情況--這就是所謂Blind trust。不過這個情況,以往不是沒有發生過:去年意大利名指揮阿巴多去世後,也曾發生過通訊社誤發另一意籍鋼琴大師波里尼的照片,結果全球不少傳媒也一起烏龍的趣事,吾友朱振威也曾撰文記之。
當然,這個調查結果還是很粗疏的,其他人可能有更透徹的觀察。
五月十日更新:
友人告知,原來星島日報歐洲版,在三月報道地方政府大臣白高志,出席英國保守黨華人之友的春茗時,就有提過「麥大粒」之名。
至於這是不是源頭,以及《世界日報》記者據此引述麥大粒之名,真的是莫宰羊了,就讓我們將這個尋找源頭的遊戲,繼續玩下去吧!
今次大選另一個焦點,是所有選前民調機構集體搞錯,令人人原本以為保守黨及工黨叮噹馬頭,但最後卻謬之千里。不過其中一個有份進行民調的機構,卻在選後承認,他們在選前一日所做的最後民調,其實與選果結果相差無幾,但是卻沒有公布,如此做法是不想自摑咀巴,還是不想落同行的面子而沒有出版?不過機構承認,正因為最後民調與之前相差太大,他們最後退縮,也可以說是民調研究的一次經典案例了...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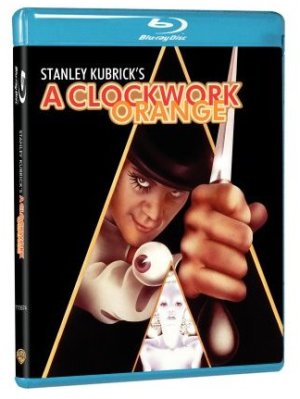 後奧運的日子,電視節目回復正常,但來來去去也是千篇一律,不看也沒有太大損失,還是看影碟較為「實際」。日前閒逛唱片店,見到
後奧運的日子,電視節目回復正常,但來來去去也是千篇一律,不看也沒有太大損失,還是看影碟較為「實際」。日前閒逛唱片店,見到 工作多多少少與翻譯有關。一直覺得,若然一個未看過原文--語言寫成的東西--的人,在對最初的文本一無所知的情況下,看到譯文也可以懷著百分之一百信心說,「這段東西寫錯了,譯錯了」的話,那末譯者在這段文字的工夫,可算是徹徹底底的失敗了。不幸地,本年看過好幾本國內譯的書,都給我遇上這個情況。
工作多多少少與翻譯有關。一直覺得,若然一個未看過原文--語言寫成的東西--的人,在對最初的文本一無所知的情況下,看到譯文也可以懷著百分之一百信心說,「這段東西寫錯了,譯錯了」的話,那末譯者在這段文字的工夫,可算是徹徹底底的失敗了。不幸地,本年看過好幾本國內譯的書,都給我遇上這個情況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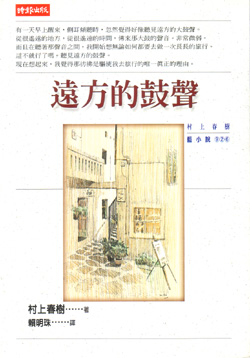 附注中「這裡的小說」是指村上在文中「在那裡一點一點地把小說做最後的修正」(頁一五一)。但是村上所寫的「小說」,卻絕不是賴明珠所言的《挪威的森林》,而是《挪》之後的《舞舞舞》,村上春樹亦在<倫敦>中寫到,他在倫敦將列印出來的《舞.舞.舞》小說原稿寄到東京(頁二九二)!也即是說,好好的不加任何附注還好,這樣加了以後,卻搞出一個大烏龍,大錯處。
附注中「這裡的小說」是指村上在文中「在那裡一點一點地把小說做最後的修正」(頁一五一)。但是村上所寫的「小說」,卻絕不是賴明珠所言的《挪威的森林》,而是《挪》之後的《舞舞舞》,村上春樹亦在<倫敦>中寫到,他在倫敦將列印出來的《舞.舞.舞》小說原稿寄到東京(頁二九二)!也即是說,好好的不加任何附注還好,這樣加了以後,卻搞出一個大烏龍,大錯處。

Recent 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