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在「讀《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》(上)」的末部,本來開了期票,說要在下篇談一下有關藤井省三,在書中評論兩岸三地的村上譯者的篇章,但是過了這麼久,才肯動筆寫下篇,真是自己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(主要是自己太懶的緣故...)。
在「讀《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》(上)」的末部,本來開了期票,說要在下篇談一下有關藤井省三,在書中評論兩岸三地的村上譯者的篇章,但是過了這麼久,才肯動筆寫下篇,真是自己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(主要是自己太懶的緣故...)。
在讀《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》之前,也約略知道有關藤井省三,對國內譯者林少華的譯筆有微言的情況。七月時,讀到《明報》世紀版中一篇《林譯村上:零分》的文章,林少華在文章中,反駁藤井省三在《村》中對他的批評,不過自己後來讀了這本書的第五章(〈百家爭鳴的翻譯森林--中國、香港、台灣譯本的比較〉,下文簡稱〈百〉)後,倒沒有藤井省三簡化地將林譯評為「零分」的印象--這可能是林少華自己有點反應過度--但是作者崇賴明珠(某程度上也包括葉蕙)貶林少華的意圖,確是十分明顯的。
私見認為,要評論一個已翻譯同一名作家多本著作的譯者的文筆,比較的範圍應該可以再廣一些。在村上春樹中譯的例子中,林少華及賴明珠都譯了相當數量的村上著作,如果單以一本《挪威的森林》去比較兩者熟優熟劣,好像有點「點到即止,意猶未盡」的感覺。
我這樣說的原因,是因為村上春樹作品涉及的文體有不少,小說固然有之,散文甚至類廣告文宣的東西也有,不同文體要求的譯法也有不同,好像是讀《挪威的森林》而言,我自己是不折不扣的葉蕙版(博益)的支持者,賴明珠的版本一直有點抗拒,但是賴明珠譯筆下的《朝日堂》系列,以至村上的遊記等,自己反而十分接受(雖則也有「畫蛇添足」的事件發生)。或者是限於篇幅吧,如果藤井用來比較的範圍更大的話,結果可能會更好。
〈百〉的重點,在於翻譯的老問題「信、達、雅」。藤井省三認為,林少華特別重視「雅」而「稍微疏忽了所謂『信』的正確度」(頁二二七,所引頁數均係台北時報文化版)。讀到這個「信達雅」這個概念,我反而重讀了一次《傅雷與他的世界》(下左圖,金聖華編,香港:三聯書店,一九九四年)這本書,因為想起了傅雷經常提及,「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」(《傅》頁二一六),及「重神似不重形似,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」(前引書頁二零八)的目標--得承認,工作或多或少涉及翻譯的本人,是對這兩句是心悅誠服的,雖則自己「段數」太低,在實踐時永遠落得一榻糊塗。
 如果將「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」這句話,作為譯者追求的目標,那麼放在村上作品中譯的情況,又應如何是好?假如村上春樹用中文寫作的話,他會用上他的口語文學體,還是用「優雅」、一如林少華譯筆下的文體?當然,如果是賴明珠的擁躉,又或是完全支持藤井省三的觀點的話,選擇當然會是前者,但在這個假設性甚高的問題中,加上我們又不是村上本人,大概我們的答案,都不會是最權威的唯一標準吧。
如果將「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」這句話,作為譯者追求的目標,那麼放在村上作品中譯的情況,又應如何是好?假如村上春樹用中文寫作的話,他會用上他的口語文學體,還是用「優雅」、一如林少華譯筆下的文體?當然,如果是賴明珠的擁躉,又或是完全支持藤井省三的觀點的話,選擇當然會是前者,但在這個假設性甚高的問題中,加上我們又不是村上本人,大概我們的答案,都不會是最權威的唯一標準吧。
既然如此,「村上的中文寫作」會是怎樣的樣子,到了譯者手上,很可能涉及一個推敲的過程,去推度村上懂中文的話,他會如何寫這些句子、篇章。不過,這畢竟涉及非常重的個人主觀成份,例如我們心目中的「文學中的中文」是怎樣子,等等,都會影響結果。林少華及賴明珠如何看待村上中譯,都可能受他們的教育,及多年積聚下來的文學觀、翻譯觀所影響,因而得出不同的結論,也就造就不同的文體。至於哪個更優勝,亦恐怕是各有各看法,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吧。
其實,從林少華及賴明珠的譯文差異,也可以看出「對原著忠實vs譯者譯文風格」的問題。明顯地,林少華的「濃妝」是明顯將他的風格加進村上的原著中,而賴明珠的譯筆,是不折不扣的忠於原著。我自己讀這些譯本的經驗,是總覺得賴明珠的譯本「不太像中文」,反而林少華的版本「好像順暢得多」,這也是我曾經有一段時間--大約是八、九年前左右--專注的看林少華版,而遠賴明珠版的原因。換個方式說,我對林少華的「風格」沒有太大的反感(反而是職業病使然,自己對譯錯東西的「硬傷」就極為反感),只是「過與不及是隨時隨地都可能有的毛病」(傅雷致林以亮書,見《傅》頁三零二),但老實說,我沒有那種對濃妝是否太過的敏感,這也許是我一致覺得林少華的譯文「也可以讀」的緣故。
藤井省三的〈百〉中,提到人名翻譯的問題,以「直子」、「綠」及「木月」作例之餘,又稱讚賴明珠作出「無微不至的顧慮」(頁二二二)。藤井認為,在《挪威的森林》中,主角的名字「具有深刻的象徵」,所以有用片假名的做法,但批評林少華將名字全譯為漢字,是封閉「更深入解釋的可能性」(頁二二五)--奇怪,其實葉蕙也是全譯為中文的,但是為何藤井只針對林少華?誠然,小說作為文學創作,處處也可見到作者的心血,對於讀者而言,處處也有解讀的空間,不過如果說《挪》中的人物的名字用上片假名,藉以讀音去引導讀者,去作出其他聯想的話,換成中文的話,應該如何處理?
譯者的責任,是引導不懂原作語言的讀者,去領會原作,這個說法應該沒有太多人反對,不過涉及到「對等」的問題時,在中文譯本中,將片假名變成羅馬拼音,雖然在形式上是跟隨了原著,但是對於不懂日文的人(包括在下)而言,還是領略不了當中暗含的喻意,未能達到「全面對等」的目標--看到通篇都是Kizuki,真是一頭霧水的(雖然村上也對賴明珠說,翻成英文好了)。在中文而言,這可能要用上「諧音」甚或「食字」的做法,才有可能解決這問題吧,不過自己會認為,用上譯注,或是統一用上中文,會是比較保險的做法。藤井的批評,好像是吹毛求疵了些。
 至於藤井在〈百〉中,指林少華有「中文國族主義思想」,以至林少華在〈林譯村上:零分〉之間「罵戰」,在我看來,實在有點無聊。我奇怪的是,藤井省三對於林少華的批評,已不止於文舉的分析,而是包括分析他的出身、經歷後,得出「不得已才搞翻譯」等等的結論,但這實在有點欠缺說服力。不過同樣地,我自己也覺得,林少華本人也太boast了些,好像上周出版的U Magazine中,林少華在〈尋找村上春樹:賴明珠X林少華〉中,他那些「讓我淪落成翻譯家」之類的說法,也令我對他「另眼相看」。看來林少華還是說少點較好。
至於藤井在〈百〉中,指林少華有「中文國族主義思想」,以至林少華在〈林譯村上:零分〉之間「罵戰」,在我看來,實在有點無聊。我奇怪的是,藤井省三對於林少華的批評,已不止於文舉的分析,而是包括分析他的出身、經歷後,得出「不得已才搞翻譯」等等的結論,但這實在有點欠缺說服力。不過同樣地,我自己也覺得,林少華本人也太boast了些,好像上周出版的U Magazine中,林少華在〈尋找村上春樹:賴明珠X林少華〉中,他那些「讓我淪落成翻譯家」之類的說法,也令我對他「另眼相看」。看來林少華還是說少點較好。
說到底,不同的譯法沒有對與錯。反正村上自己本人也說過,他在乎的是翻譯的速度,即使譯文有點「差異」(a little off)也沒有所謂,又認為他不太擔心「語言表達的細節程度」(details at the level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),總之他對於作品獲翻運感到開心(Jay Rubin,頁三一一),爭著將林少華的譯文,說得近乎一文不值的程度(對呀,我的感覺是藤井在〈百〉中是去「插」林少華的),好像是有點怪了。
傑魯賓也在《聽見100%的村上春樹》(上右圖)說過,「譯者的主觀處理,無可避免地扮演重大角色」,他自己也提到,自己譯的村上著作,與伯恩邦及Phil Gabriel的譯本也有不同的風格,亦承認伯恩邦的 “exaggerated hipness of expression” 有助《尋羊冒險記》吸引西方讀者的注意(Jay Rubin,頁三二零)。如果村上本人在乎的是作品的傳播(當然,準確是重要的前提),而林少華的中譯版--在我而言--也不致於錯得離譜的情況下,我難免對藤井省三的說法有一點保留。
Like this:
Like Loading...

 我想,對於此地的新聞工作者來說,每年一到十月初,會是相當「頭痕」的時候--諾貝爾獎的得主名單,在個多星期之內陸續公布,但是每日傍晚守候在電腦前,看到通訊社傳來得獎人名稱時,都會有數個疑問:他/她/他們是誰?要如何解釋得獎主的成就?偏偏科學類獎項的得獎者,所進行的研究不是一時三刻,就可以理解的(畢竟熟悉科學的人比較少),要深入淺出地向讀者/觀眾解釋,實在是一件苦差。
我想,對於此地的新聞工作者來說,每年一到十月初,會是相當「頭痕」的時候--諾貝爾獎的得主名單,在個多星期之內陸續公布,但是每日傍晚守候在電腦前,看到通訊社傳來得獎人名稱時,都會有數個疑問:他/她/他們是誰?要如何解釋得獎主的成就?偏偏科學類獎項的得獎者,所進行的研究不是一時三刻,就可以理解的(畢竟熟悉科學的人比較少),要深入淺出地向讀者/觀眾解釋,實在是一件苦差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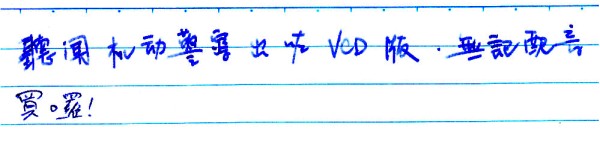
 在
在 如果將「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」這句話,作為譯者追求的目標,那麼放在村上作品中譯的情況,又應如何是好?假如村上春樹用中文寫作的話,他會用上他的口語文學體,還是用「優雅」、一如林少華譯筆下的文體?當然,如果是賴明珠的擁躉,又或是完全支持藤井省三的觀點的話,選擇當然會是前者,但在這個假設性甚高的問題中,加上我們又不是村上本人,大概我們的答案,都不會是最權威的唯一標準吧。
如果將「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」這句話,作為譯者追求的目標,那麼放在村上作品中譯的情況,又應如何是好?假如村上春樹用中文寫作的話,他會用上他的口語文學體,還是用「優雅」、一如林少華譯筆下的文體?當然,如果是賴明珠的擁躉,又或是完全支持藤井省三的觀點的話,選擇當然會是前者,但在這個假設性甚高的問題中,加上我們又不是村上本人,大概我們的答案,都不會是最權威的唯一標準吧。 至於藤井在〈百〉中,指林少華有「中文國族主義思想」,以至林少華在〈林譯村上:零分〉之間「罵戰」,在我看來,實在有點無聊。我奇怪的是,藤井省三對於林少華的批評,已不止於文舉的分析,而是包括分析他的出身、經歷後,得出「不得已才搞翻譯」等等的結論,但這實在有點欠缺說服力。不過同樣地,我自己也覺得,林少華本人也太boast了些,好像上周出版的U Magazine中,林少華在〈尋找村上春樹:賴明珠X林少華〉中,他那些「讓我淪落成翻譯家」之類的說法,也令我對他「另眼相看」。看來林少華還是說少點較好。
至於藤井在〈百〉中,指林少華有「中文國族主義思想」,以至林少華在〈林譯村上:零分〉之間「罵戰」,在我看來,實在有點無聊。我奇怪的是,藤井省三對於林少華的批評,已不止於文舉的分析,而是包括分析他的出身、經歷後,得出「不得已才搞翻譯」等等的結論,但這實在有點欠缺說服力。不過同樣地,我自己也覺得,林少華本人也太boast了些,好像上周出版的U Magazine中,林少華在〈尋找村上春樹:賴明珠X林少華〉中,他那些「讓我淪落成翻譯家」之類的說法,也令我對他「另眼相看」。看來林少華還是說少點較好。

Recent 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