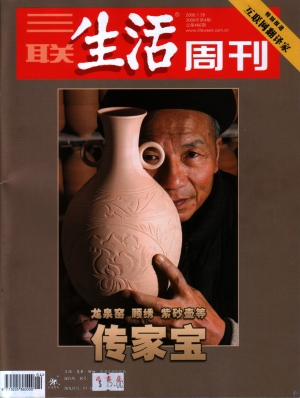 我喜歡讀歷史書及傳記類書籍,但可沒有接正統的歷史學訓練--中國歷史及西史科,也是讀到中五就停止。所以對於所謂史學的研究、採集、整理方法,我可是一竅不通的。或者五零一房東或船山先生,可以就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賜教賜教。
我喜歡讀歷史書及傳記類書籍,但可沒有接正統的歷史學訓練--中國歷史及西史科,也是讀到中五就停止。所以對於所謂史學的研究、採集、整理方法,我可是一竅不通的。或者五零一房東或船山先生,可以就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賜教賜教。
問題是這樣的:二零零八年第四期的《三聯生活周刊》(一月廿八日刊)的「口述」專題,訪問了清代肅親王善耆的第三十八名孩子愛新覺羅.顯琦(金默玉)。最初不知道這位「格格」是誰,讀下去才發現她是川島芳子的妹妹--說起來也真慚愧,對於川島芳子,我只知道李碧華曾寫過一本有關她的書,或梅艷芳主演的電影(都沒有看過、讀過),卻不知道她原是滿人之後。金默玉在長達六頁的訪問中,由她小時的生活說到她後來遭拘捕,在秦城監獄待了十五年的經歷,可說是挺有趣的,不過讀到當中某些段落,卻發現有些問題。
例如文章的引言說:「一九一八年,流亡予旅順、仍沉浸於恢復大清帝業的肅親王善耆迎來了他的第三十八個孩子,他為這個小生命取名為愛新覺羅.顯琦」。然後金默玉口述歷史的第一句,就是「一九二二年父親去世時,我只有四歲,所以我對父親沒什麼印象」。(均為一零二頁)假設這個兩個關於年份及歲數的論述是正確的話,到了第一零四頁時,金默玉說他父親去世後三年還葬北京的那段就有趣了:
父親去世三周年時,被運回北京安葬...送葬的親友多達數百人,因為隊伍太長,從旅順家中到火車站整整用了一天。靈柩用火車經奉天、山海關到達北京,是袁世凱親自在車站迎接的。
善耆在金默玉四歲時去世,他去世後三年遷葬北京,而金默玉是在一九一八年出生的,按道理遷葬那年應該是一九二五或二六年吧。但是袁世凱是在一九一六年病死的,兩個年份相差了近十年。相比之下,應該是金默玉的論述有誤吧?最妙的是,金默玉及後提到川島芳子(愛新覺羅.顯玗)時,說她嫁給蒙古王公的二子時,又提到「一九一六年,袁世凱暴亡後」(一零五頁),同一篇文章的前後矛盾是很明顯的。
又或如金默玉提到「末代皇帝」溥儀時,第一句就是說他「一九三一年溥儀從北京逃出來後,先在旅順躲了一段時間」(一零四頁)。但是如果對溥儀的生平有點認識,又或是讀過他的自傳《我的前半生》的話,都會知道他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(是民國十三年的事)後,是逃到天津,最後到九一八事變後,到了東三省的滿洲國當起皇帝來的。可以肯定的是,溥儀絕不是在「一九三一年」逃出北京的--因為溥儀本人也說過,他「到天津來的目的原是為了出洋,結果卻一連住了七年」(《我的前半生》頁一四五,香港廣角鏡版),但後來在一九三一年底到了旅順(見該書第五章「潛往東北」的描述)。
讀了這篇文章,我的疑問是,作出記錄、整理這些口述歷史的人,在面對明顯不過的事實錯誤時,他們應該採取甚麼動作呢?是尊重口述者照錄無誤,還是提醒口述者有問題作出更正,還是以事後「編按」的形式,去提供另一個說法給讀者呢?我這樣提出的原因,或者是職業病使然吧,因為見到與事實有明顯出入的東西,就自然會起「改了它吧」的念頭,見到《三聯生活》的編輯們隻字未改/不改,總是覺得有點奇怪的。
另一方面,我也不能保證溥儀所說的也是百分百分的事實,只是覺得無論是讀歷史或是看新聞,看多數個資料來源/版本,對事情的全貌總有一個更廣闊的了解。此時起想前中國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夫人章含之去世的消息,章含之那本《跨過厚厚的大紅門》我也讀過,她說了不少與第二任丈夫,亦即是喬冠華的的故事,但是她對於喬冠華後來如何被整,又或是她與第一任丈夫的事也很少提及。後來有次經過書店,發現其前夫洪君彥所寫的《我和章含之離婚前後》,不就是從另一個角度寫這些人和這些歷史嘛,不過那時沒有買下,現在其中一人已去,或者找時候買這本書,拿來與《跨》來對照看看。
洪君彥的文章,曾在二零零四年於《明報》刊載。當時馬家輝為文介紹時寫道:
基於立場角度的殊異分歧,同一個故事可能會出現不同的版本,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?歷史述說本就該是眾聲喧嘩,歷史的真相經由不同的述說選材而有機會逐漸成形,她說她的,他說他的,而我們,透過別人的故事而認識歷史,自該哀矜毋喜。
(〈她們說完了,輪到他開口〉,《明報》D8版,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二日)
確然。讀歷史,看新聞,應該還是多看幾個版本,才敢妄下論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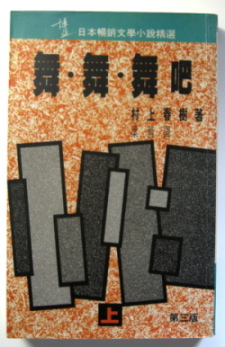
 噢,談遠了。讀了數年博益版的村上春樹後,父親的朋友「勸告」我應該看看台灣版的村上,於是漸漸也購進了一堆,造成置頂圖像的「盛況」,不過當年(應該是九六年吧?)博益出版《夜之蜘蛛猴》時,宣傳要與日本版一模一樣的設計出版,於是也有一點期待,更特地託家中附近一間書店為我「留書」,以免在出版時買不到(可想而知當年本人是多麼無聊!)。後來書出版了,但是那時讀的多是村上的長篇小說,對從未接觸這些「小小說」的我而言,初看時是有點不慣的,賣書給我的書店老闆也覺得「有點怪」。不過那時十多年前的情況了,現在讀多了村上的作品,種類也不只是小說,還有散文、雜誌短文、遊記及插圖文章時,也覺得《夜之蜘蛛猴》是十分「過癮」的作品了。
噢,談遠了。讀了數年博益版的村上春樹後,父親的朋友「勸告」我應該看看台灣版的村上,於是漸漸也購進了一堆,造成置頂圖像的「盛況」,不過當年(應該是九六年吧?)博益出版《夜之蜘蛛猴》時,宣傳要與日本版一模一樣的設計出版,於是也有一點期待,更特地託家中附近一間書店為我「留書」,以免在出版時買不到(可想而知當年本人是多麼無聊!)。後來書出版了,但是那時讀的多是村上的長篇小說,對從未接觸這些「小小說」的我而言,初看時是有點不慣的,賣書給我的書店老闆也覺得「有點怪」。不過那時十多年前的情況了,現在讀多了村上的作品,種類也不只是小說,還有散文、雜誌短文、遊記及插圖文章時,也覺得《夜之蜘蛛猴》是十分「過癮」的作品了。
 房中買了五年多的微型音響組合,當中的CD部分早已壞了--應該是壞了兩年多--但是一直都沒有意欲去換一部新的或拿去修理。原因一來是聽唱片的模式早已改變,唱片買回來以後,第一個動作是塞進電腦內轉成電腦檔案,然後上傳到iPod聆聽;二來我那部音響,除了唱片機以外,其他部分仍然十分健壯,包括Mini Disc的部分。
房中買了五年多的微型音響組合,當中的CD部分早已壞了--應該是壞了兩年多--但是一直都沒有意欲去換一部新的或拿去修理。原因一來是聽唱片的模式早已改變,唱片買回來以後,第一個動作是塞進電腦內轉成電腦檔案,然後上傳到iPod聆聽;二來我那部音響,除了唱片機以外,其他部分仍然十分健壯,包括Mini Disc的部分。 也記得大學最後一年,竟然有幸給我「抽」到李天命的課堂(那時只是姑且一試,但是給我成功登記他的通識課)。由於機會十分之難得,每次上課都必備物品,除了紙筆以外,就是我那部有錄音功能的Mini Disc播放機,還要將錄音模式設定成單聲道的Long Play,以將Mini Disc的錄音時間變長至兩小時以上,一氣呵成將整個課錄下。如果有事不能上課的話,也要特地將播放機交給同學,託他幫我代錄,以免「走寶」!不過有趣的是,不但是我們一眾學生都將李天命的課堂進行錄音(的確為數不少),就連李天命本人每次上課前,也將錄音咪扣在衣服上--據他所說,是出版社的要求,然後順道作一點抱怨。
也記得大學最後一年,竟然有幸給我「抽」到李天命的課堂(那時只是姑且一試,但是給我成功登記他的通識課)。由於機會十分之難得,每次上課都必備物品,除了紙筆以外,就是我那部有錄音功能的Mini Disc播放機,還要將錄音模式設定成單聲道的Long Play,以將Mini Disc的錄音時間變長至兩小時以上,一氣呵成將整個課錄下。如果有事不能上課的話,也要特地將播放機交給同學,託他幫我代錄,以免「走寶」!不過有趣的是,不但是我們一眾學生都將李天命的課堂進行錄音(的確為數不少),就連李天命本人每次上課前,也將錄音咪扣在衣服上--據他所說,是出版社的要求,然後順道作一點抱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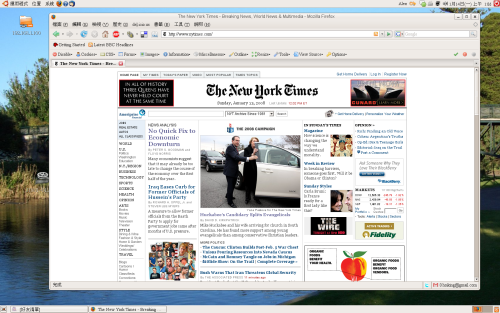
 好像此地經常出現的言論,是兩大超市集團分店愈開愈多,令小型商店的生存空間日窄;又或是連鎖式快餐廳成行成市,令人吃東西的選擇日少;但是倒很少到一些聲勢浩大的論述,指
好像此地經常出現的言論,是兩大超市集團分店愈開愈多,令小型商店的生存空間日窄;又或是連鎖式快餐廳成行成市,令人吃東西的選擇日少;但是倒很少到一些聲勢浩大的論述,指

Recent 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