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說起來,從事翻譯的人應該多謝「巴別塔」的存在,若然《聖經》舊約中的人,沒有興建它的念頭,上帝就不會被觸怒,也不會將所有人變得「雞同鴨講」--如果世上只得一種語言,翻譯也自不會存在了。不過翻譯這回事確是充滿挑戰,要求高自不待言,譯者也要心思細密,不可放過任何一個可能出錯的機會,因為一不留神就會跌個粉身碎骨。
說起來,從事翻譯的人應該多謝「巴別塔」的存在,若然《聖經》舊約中的人,沒有興建它的念頭,上帝就不會被觸怒,也不會將所有人變得「雞同鴨講」--如果世上只得一種語言,翻譯也自不會存在了。不過翻譯這回事確是充滿挑戰,要求高自不待言,譯者也要心思細密,不可放過任何一個可能出錯的機會,因為一不留神就會跌個粉身碎骨。
此外譯不同類型的作品,也有不同的要求及形式,就如譯文學作品及正統學術作品,文風及格式也有不同。這是我剛讀完上年底出版、村上春樹著/賴明珠譯的《終於悲哀的外國語》(右上圖;台北:時報文化,二零零六年十一月)的感覺。
《終於悲哀的外國語》是村上在九十年代初,在美國居住時(普林斯頓大學邀請他當駐校作家)為日本雜誌所寫的隨筆。寫《終》時的村上,剛在歐洲過了三年的旅居生活,然後又即刻搬到美國,但是《終》的文體與旅歐的作品《遠方的鼓聲》有所不同,前者對我來說是有點對美國生活的觀察,及其人對此的反思的味道(因此文章較長),而後者則有點像遊記,比較抽離。雖然如此,對於我這個「村上fans」而言,《終》仍是讀得津津有味,只是對於賴明珠的翻譯,仍是有點東西要說。
之前曾就不同人的村上作品翻譯,寫過一點文章,當時指的是不同譯者對原文的理解,至於這一篇,說的是譯者對外國文化認識未夠透徹,就會跌進陷阱。譯村上的作品,不只涉及日文及中文兩種文章,很多時候也涉及英文,正因為村上春樹本人已經夠「外向」,加上《遠方的鼓聲》及《終於悲哀的外國語》之類的書,都涉及外國生活的經驗,結果形成村上先從外國語翻譯至日文,譯者再由日文原著譯至中文的情況,這種英文→日文→中文的過程,往往為譯者構成一個難題:究竟在譯英文原詞時,應該直截了當寫英文原字後加譯名,還是譯了後再加附注、譯注?
對我而言,哪一種做法都沒有所謂,但是要全書統一。不過在讀賴譯的《終》時,卻發現一個問題,就是她的譯本中,一時只寫英語名詞,一時先中後英,一時先英後中,一時只寫中文名詞,看得我頭昏腦脹。例如在<美國版團塊世代>一文中就有這樣的例子:
「...就像辛西雅在電話裡說的那樣,他們家雖然養有馬及山羊,不過並沒有在生產什麼。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『住在農場裡』的這種生活姿勢。遠離都會生活,在大自然中和平地過日子這個事實。如要要勉強分類的話,也許適合用『後雅痞』(post yuppie)這個詞彙來稱呼他們的生活樣式吧(譯注:在英文中,雅痞原來是yup,即young urban professionals的簡稱)。在雷根總統在位前後景氣繁榮「隨便你做什麼都賺錢」時代的美國,住在大都市的市中心、上高級餐廳或夜總會、開高級汽車、過著流行最尖端的閃亮生活,對美國年輕世代來說是最時髦的象徵。(想要了件這種生活樣式典型的話不妨閱讀布列特.伊斯頓.艾利斯〔Bret Easton Ellis〕寫的《美國殺人魔》。作品的評價雖然完全兩極化,不過以社會狀況來說,難得有這樣自我犧牲式的嘲諷性小說。因為《走夜路的男人》雖然嘲諷,但至少不是自我犧牲式的小說。)...」(頁四十二)
當然,我沒有看過村上的日文原著,不知道他寫這一後時,會不會是寫得這樣「複雜」的,但是我總覺得,翻譯是一種「再創作」的過程,譯者就是代作者,以後者不熟悉的語言,將原文呈現給讀者,這不只涉及將語言A轉到語言B這麼簡單,還包括為作者將作品去蕪存青的工作。另一方面,在解釋複雜的東西時,加譯注是必需的做法,但是畢竟文學作品不是嚴肅學術作品,斷沒理由要讀者看小說時就如看學報般,每版注釋所佔版面,比原文還要多。
如果原文是「日文譯名(英文原名)」的話,譯成「中文譯名(英文原名)」是最上乘的做法,如果只有日文譯名的話,我想用上「中譯(英原)」的做法會較為恰當--雖然我知道《美國殺人魔》就是香港曾上映過的電影《美色殺人狂》(American Psycho)的原著,但是《走夜路的男人》究竟是啥?沒有了英文名字,我等讀譯本的人真的隨時陷入迷宮。
《終於悲哀的外國語》不少段落都有涉及電影,如<描寫卡佛鄉的勞勃.阿特曼的迷宮電影>,然而兩岸三地對電影的片名譯法不同,我想上段提出的譯名問題,在這篇顯示得更清楚。諸如《超級大玩家》(頁一五六)、《巴頓芬克》和《裸體午餐》(頁一五七)、和《殺無赦》(頁一六零》,都是我猜來猜去也想不到原名是甚麼的電影,但是又看到賴明珠譯人名時,只是一概寫英文名字,真是有點奇怪。
不過最驚訝的,還是頁十寫日本汽車時的一段:「說到『有一點奇怪的事情』,去年的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紀念日,有一位專欄作家安迪.路尼(Andy Runy)(他的專欄集在日本也有譯文,所以可能不少人知道他的名字)寫了一篇不可思議的反日專欄。」Andy Runy在網絡中遍尋不獲,會不會是在《六十分鐘》(60 Minutes)中每集結尾時,嬉笑怒罵世事的Andy Rooney?


 記得《叮噹》(對不起,我老餅,絕不叫這套漫畫做《多啦A夢》)中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:大雄被技安欺負,吃噹拿出一個像是印章的東西,只要將特定的圖型寫上去,再將印章印在技安的背上,他看到任何與該圖形有關的物件,如印章畫上圓形的話,就會產生恐懼症--嘿,我想寫有關《叮噹》的文字,也不會被人控告侵權吧?!
記得《叮噹》(對不起,我老餅,絕不叫這套漫畫做《多啦A夢》)中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:大雄被技安欺負,吃噹拿出一個像是印章的東西,只要將特定的圖型寫上去,再將印章印在技安的背上,他看到任何與該圖形有關的物件,如印章畫上圓形的話,就會產生恐懼症--嘿,我想寫有關《叮噹》的文字,也不會被人控告侵權吧?! 特首佘當奴--噢,不是,應是一名「正在積極準備參選的人」(《東方日報》引曾蔭權競選特首辦發言人語),昨日高調巡視一個「妾身未明」,連主人會不會使用也是未知數(理論上如此)的「競選辦公室」,事後這名「正在積極準備參選的人」稱,他每日「廿四小時都是特首」,沒有公餘或私人時間,因此下午三時以此身份到訪辦公室,沒有問題,云云。這一幕,端的是洋洋大觀,政治確是the art of possible也。
特首佘當奴--噢,不是,應是一名「正在積極準備參選的人」(《東方日報》引曾蔭權競選特首辦發言人語),昨日高調巡視一個「妾身未明」,連主人會不會使用也是未知數(理論上如此)的「競選辦公室」,事後這名「正在積極準備參選的人」稱,他每日「廿四小時都是特首」,沒有公餘或私人時間,因此下午三時以此身份到訪辦公室,沒有問題,云云。這一幕,端的是洋洋大觀,政治確是the art of possible也。 真不知道,假如
真不知道,假如
 今日讀
今日讀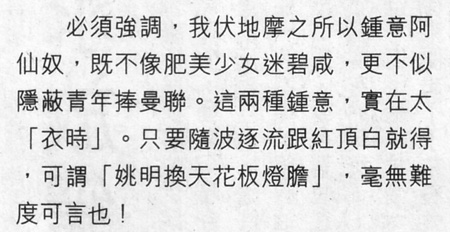


Recent 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