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往有云「黃金當爛銅」,這次圓明園獸首在巴黎拍賣,倒是將這句話調轉過來了。當然,兩個獸像都不是「爛」銅。
*北京對兩個獸首遭拍賣反應強烈,明言「打著人權的旗號侵犯中國人民的基本文化權利,這本身就是荒謬的」,雖是指摘提出有關論調的貝爾熱,將事件政治化,但是觀乎中國的舉措,都有政治化的味道。周二早上,看中央電視台的《朝聞天下》,竟然花了八分鐘去報道劉洋等人,在巴黎提出申請禁制拍賣失敗的新聞,八分多鐘花在同一宗消息上,足見央視這個官方喉舌,對事件重視程度之高,當下第一個閃過的念頭,就是北京有意「玩大」這宗事件--與早前溫家寶訪歐而不到法國,還有批抨薩爾科齊會見達賴,自是一脈相承。
*今日(周三)《文匯報》的社評說,
中國政府在堅決反對拍賣圓明園文物的同時,也要堅決表明不高價回購的立場,剎住炒作風,促使拍賣價回落,該出手時再出手。
這種論調,早前圓明園的宗天亮,接受美聯社電視台的訪問,亦作出同樣的表示。但是《文匯報》認為,中國堅拒不回購兩個獸首,就可以促使拍賣價回落,就無異是異想天開。拍賣是買賣雙方「你情我願」的活動,價高者得,端的是自由市場的最佳表現,但是中方既不是賣家,也不願做買家,又何來影響需求,致使在價格制訂上有影響力?由星期一開始的拍賣,聖羅蘭不少收藏品的賣家都高得驚人,一幅馬蒂斯作品,賣了三千二百萬美元,佳士得也將兩個獸首,定價八百至一千萬歐元,以兩者的「名氣」,肯定拍賣一方,對兩者可以至少這個價錢拍出信心滿滿(結果各賣了一千四百萬歐元!),「剎住炒風」,又如何是中國官員的主觀願望能成事?別那麼傻氣、天真罷!
*圓明園十二個獸首,五個下落不明,五個現存中國,另外兩個就是周三拍賣的鼠首、兔首。在中國的五個,都是過去由商人買下轉交中國的,當然鼠首兔首都可以用這個方法買下,只差北京(間接)動員哪個商人、公司出款買下而已,不過中國在這次事件中,將「誓不競拍」的叫價提升得如此之高,是不是就是要做成這一個既定事實:就是要讓兩個獸首被外人買下,再以此去塑造被外(尤其是法國)「迫害」的情況,好為其他外交及政治目的服務?
*林行止在《信報》周一的專欄中,提出《金剛經》及現藏大英博物館的艾爾琴石雕都是「人類公共財」的說法,如果兩個獸首都亦作如是觀,當然在人人都可到的博物館,是它們的最佳收藏點。以此推述,中國政府更應該出錢出力,將兩個獸首買回來。明知從外交、法律途經,追討流失文物,成功機會絕無僅有(有的話,艾爾琴石雕早已回歸雅典衛城了),唯一可行的合法途經,就是在商業場所買下,但是礙於「民族志氣」,為自己局限了轉圜的餘地,豈非太笨?
*說起艾爾琴石雕,記得在謔為「國際大賊竇」的大英博物館參觀時,在收藏石雕的場館,發現館方印發的說明書,就他們對於雅典政府,多年來申索還回石雕的立場作回應(及反駁),強調自己當年合法得來。其中一個理據說到,巴特農神殿已是廢墟,即使石雕回家都效用有限。當然,說不定圓明園的獸首,當年英法聯軍攻華時,沒有搶走的話,但在後來的戰亂以至文革,也難保不會被破壞(尤以文革為甚),但這種理據在我眼中,都是欠缺說服力的。個人的意見:我支持石雕回歸希臘,也支持獸首回歸圓明園。
*獸首作為藝術品/文物,公開展示總比私人小眾欣賞好,最新消息(周四凌晨三時多)是,一名電話買家用了二千八百萬歐元買下它們。不知道買家的身份,如果還是好像以往聖羅蘭般,就這樣放在自家的話,那就未免太可惜了。不禁再次聯想起,有關艾爾琴石雕的爭論。去年十一月《金融時報》一篇文章,作者建議英希兩邊的博物館,互借巴特農神殿的文物給對方展出,好營造一點友好氣氛,但是英國那邊它早表明,他們是願意借出的,只是前提是希臘承認他們有擁有權--以此投放到現在的情況,猜想中國方面,即使新買家(如果不是甚麼愛國商人/公司買下,並轉交中國的話)有願意借出到中國展示的想法,恐怕事事驚恐國民感情,會受到傷害的官員們,都會像希臘般拒絕罷--因為這等同承認,外國人擁有是合法的,國寶丟失的罪名,誰也負擔不起。
總之,都是氣節問題礙人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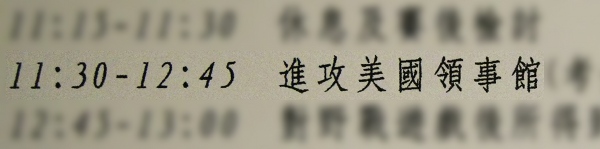

 星期四早上看到
星期四早上看到

Recent 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