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以往只有《號外》編輯才懂得的名堂,現在每個《壹本便利》的讀者都會拋了;以往只有高官富商才知道的『內幕』,現在上兩期的周刊已說過了;以往只有大歌星才會的喉震音,現在四歲的小朋友也懂了。這便是資訊發達,『人與人之間更為平等』了。...但當人人懂得的都一樣多,都一樣,都問你:『喂你睇左今期咩野未?』時,我們感覺不到沐浴天堂的快樂,卻像浸大一窩跟自己體溫一樣,跟自己體味一樣的暖湯裡,溫溫吞吞,混混噩噩...」
(謝立文:《麥嘜算憂鬱亞熱帶》)
從來都是《港燦筆記》的「忠實讀者」。佩服港燦兄對世事的觀察,喜歡他下筆的調子,往往一句起兩句止就將整件事勾畫出來,與我下筆囉唆,兜來兜去也未入正題的累贅風格很不同。最近讀到他發表的《隱蔽青年》一文,竟在「獨立媒體」網站引起一番討論,結果港燦兄要「靜思己過」。看罷整個討論,我竟然想起上面的那一段引文。也許是沒有甚麼關聯,總之就是記起就是了。
對於港燦兄在獨立媒體的討論中,被人罵到「體無完膚」,老實說,我是有點驚訝的。再三看《隱蔽青年》一文,除了形容那位青年口中所出的,都是「陳腔濫調」一句中所暗含的批評(其實批評也談不上)外,全文給我的印象,就是港燦兄對於這名思路清晰,答話「有紋有路」的青年,為何只關在家中不找工做,感覺有點驚訝而已。若要將這篇純粹是場面速記的東西,說是對「隱蔽青年」作為社會現象、以至「隱士」本身的攻擊,則實在是有點風馬牛不相及啦。
然而在獨立媒體的討論,卻很可能是由那名「青年甲」的誤讀所造成:單單由一個作為文章分類的Tag,就將文章定性為「港燦認為該青年『無病呻吟』」--若不是,為何在題前加此四字--那麼,一來這名讀者理解能力不足,二來真是為要港燦兄可憐,因為之後的討論,大致上都是建基於「港燦批評隱蔽青年」這個論點而發展,他卻要為此受箭,慘食「死貓」!
其實我的疑問比感嘆更多。在整個討論中,Jargon/行話/專業名詞固然「滿天飛」,還有人認為「隱蔽青年」是「語言暴力」云云,真是令我「眼界大開」。其實,當傳媒造出一個概括名稱,去形容一個社會現象時,是否必然等於將所形容的這一批人「邊緣化」、「矮化」,然後予以打擊?再者,討論者以「先有新聞透視的報道」作為「框架」,然後「港燦將鄰座青年的對話Make sense之」,這樣的因果論證,是否真的站得住腳呢?再者,討論者對工作/不工作加進了一批又一批的Variables,最後拋出一句「『自食其力』、『多勞多得』、『要有理想,腳踏實地』,跟本只是一堆堆未經思考的話」,那麼,我想問,思考過的話又應怎樣說?「天行健,君子以自強不息」這句話,是否可以掃進歷史的垃圾堆?
許冠傑歌曲《搵野做》的歌詞--「拿拿聲即刻走去搵野做/人必須知道自己既用途/唔去奮鬥你咪望有酬勞」--也許可以當成小人般「任打唔嬲」了。本人一名友人對我說:「我只覺得,如果隱蔽係暴力,失業甚至退休都可以係好暴力。」不知大鑼大鼓地批評「隱蔽青年」是語言暴力的人,對此二詞有何見解?
這一句很搞笑:「不論有否惡意,也不能改變語言暴力的事實」。若無惡意,何來暴力?(不要對我說暴力是沒有惡意的!)再者,甚麼是「語言暴力」?甚麼人遭到「施暴」?引起暴力的用語是甚麼?或許參與討論的人,在拋出這些「行話」時,可以解釋解釋,否則,陳義再高的討論,也會淪為小圈子的互相取興,或至少,限制了讀者的層面而已。港燦的文章只是描述一個社會現象,但被加上涼薄、迫害的標籤,請問當中原因為何?小弟不賢,還望諸位高賢賜教賜教。
獨立媒體的存在,當然可作為照妖鏡,照出傳統媒體的缺陷,補其不足,但這是不是等於逢傳統/大眾必反?若網站的人以此奉為圭梟,我想,我是會很失望的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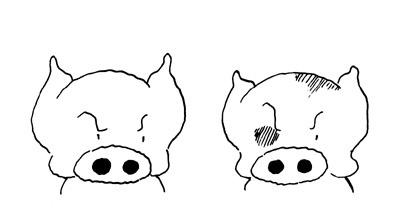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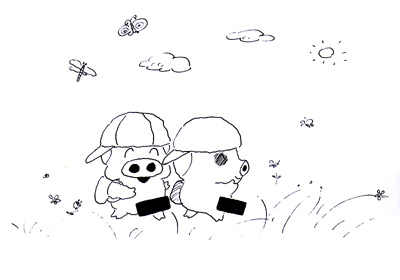





 ONE LONDON, NOT DIVIDED
(from
ONE LONDON, NOT DIVIDED
(from 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