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.10.2004
李雲迪.郎朗.音樂家
早數天在這裡轉貼了林在山訪問李雲迪的文章,想不到貼文也引來其他的人評論。其中Modern Monk提到,他較早前在紐約聽NY Phil與郎朗的音樂會時,郎朗竟在音樂會的簽名會,認出他是坐在第三行。真是有趣。
 說起來,我也曾聽過郎朗的演奏,應該是二零零二年NY Phil來港演出的事。郎朗演奏的,是拉赫曼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,指揮的是大名鼎鼎的羅連.馬素爾(Lorin Maazel)(左圖),不過得老實說,去這個音樂會,主要是因為馬素爾而不是郎朗,因為他是本人喜歡的指揮之一,尤其是二零零一年六月在倫敦聽他指揮Philharmonia Orchestra演奏馬勒第五交響曲,是我近年來最滿足、最興奮的音樂會。記得那晚「看」郎朗演奏的印象,是他的動作非常「誇張」--這也可美言為「感情充沛」,至於音樂呢,談不上很好的印象,但也絕不是差,至少不是那種會令你邊聽邊「扯火」,心裡暗罵「怎麼奏成這副德性?!」的情況。
說起來,我也曾聽過郎朗的演奏,應該是二零零二年NY Phil來港演出的事。郎朗演奏的,是拉赫曼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,指揮的是大名鼎鼎的羅連.馬素爾(Lorin Maazel)(左圖),不過得老實說,去這個音樂會,主要是因為馬素爾而不是郎朗,因為他是本人喜歡的指揮之一,尤其是二零零一年六月在倫敦聽他指揮Philharmonia Orchestra演奏馬勒第五交響曲,是我近年來最滿足、最興奮的音樂會。記得那晚「看」郎朗演奏的印象,是他的動作非常「誇張」--這也可美言為「感情充沛」,至於音樂呢,談不上很好的印象,但也絕不是差,至少不是那種會令你邊聽邊「扯火」,心裡暗罵「怎麼奏成這副德性?!」的情況。
至於李雲迪,我從沒有聽過他的現場演奏--一來票子太快售罄,二來我也沒有時間去聽--所以聽他的演出,也只能透過唱片。兩周前讀《明報周刊》(1873期),劉志剛評李雲迪最新的蕭邦作品唱片時,結論是:「本CD給我最深刻的體會是:士別三日,刮目相看,郎朗比雲迪更『勁』?未必,走著瞧。」 似乎「力量型」與「詩人型」,已成為一般人心目中,郎朗與李雲迪的最大(也是最容易歸類的)分別。當然,郎朗與李雲迪演奏的音樂也有分別,正當李雲迪以演奏蕭邦的作品「起家」時,第一次令我對郎朗這個名字注意的,是他在數年前的英國廣播公司Proms中,演奏拉赫曼尼諾夫第三協奏曲的現場錄音(右圖)!雖然我以Horowitz演奏的Rach 3為「標準版本」,但是郎朗的表現也不能不令我驚嘆。
似乎「力量型」與「詩人型」,已成為一般人心目中,郎朗與李雲迪的最大(也是最容易歸類的)分別。當然,郎朗與李雲迪演奏的音樂也有分別,正當李雲迪以演奏蕭邦的作品「起家」時,第一次令我對郎朗這個名字注意的,是他在數年前的英國廣播公司Proms中,演奏拉赫曼尼諾夫第三協奏曲的現場錄音(右圖)!雖然我以Horowitz演奏的Rach 3為「標準版本」,但是郎朗的表現也不能不令我驚嘆。
記得五月六日的《壹周刊》曾訪問了郎朗(題為《狂得起.郎朗》),當中郎朗不乏豪情壯志之語,也批評了李雲迪:「他正在開始,我希望他愈來愈好,我相信他將有很好的事業,但我的事業比他高一些。我們雖然年齡一樣,但在兩個舞台上,他不能跟我比。以我的年齡,我是全世界最好的,不論以出場費或任何角度,你可以查查。我不想炫耀,因這樣做很蠢,但你問了,我只好說現狀。」我的老實私見是:郎朗有其傲氣,李雲迪則較內斂,要我二者擇一,我寧取李雲迪而不取郎朗,這是我的個人取向及態度問題。(當然,李雲迪樣子有書卷氣,郎朗太「粗眉大眼」了,呵!)
一般人對於郎朗與李雲迪的喜惡,在於前者商業味重,後者較像藝術家--我也是其中之一。不過令我產生興趣的問題,就是一名古典音樂演奏者,是不是不可與商業這些「俗氣」的東西結合?身邊不少人認識郎朗的途經,在於他為李克勤主唱的《我不會唱歌》作伴奏,但是李雲迪也常拍商業廣告,還在最近上了無線《勁歌金曲》(?)啊?或者,這可能正是古典音樂演奏者所面對的難題:古典音樂愈來愈少人聽,連帶唱片銷售、音樂會收入也下降,要振興這門事業,演奏者唯有多作宣傳,甚至進行cross-over來推廣古典樂了,不過不少「死硬派」古典音樂迷,卻認為這種行經「離經叛道」,沾污了古典音樂這祟高的藝術!
一說到cross-over,立刻想起剛在周日於本港演出的Bond,及最近推出唱片的Vanessa Mae,還有Maskim。可能我也是一名迂腐的人,我得承認我是不喜歡這些人,總嫌他們演出的東西及方式膚淺、無聊。若說商業味重的話,相信郎朗與他們仍有相當一段距離!奇怪的是,他們都是由正統的古典音樂演奏訓練出身,但是一投身商業市場,就披上Sex Sells的外衣,以外表而非音樂本身吸引大眾了--相信各位仍會記得,Vanessa Mae那張《Violin Player》唱片,穿上濕身小背心,站在水中拉小提琴的照片罷?
 前述同期《明周》中,劉偉民在《我的音樂選擇》專欄寫道:「對於古典音樂或傳統音樂工作者,『性』似乎仍是一個禁忌。」而《誰殺了古典音樂》(左圖)的英國樂評人萊布雷希特(他在加拿大的Scena網站有定期專欄),更在書中對Vanessa Mae之流大加鞭撻:「這股風潮在陳美的身上達到了低俗的極致...這位小女孩身著貼身內衣,眯眼噘咀地對著攝影機做出老練的表情。對於一個電影女明星來說或許可以接受的行為,出現在應以音樂內涵為努力方向的音樂家,和擁有悠久傳統的唱片公司(按:EMI)身上時,實在教人難以調論。即使是見多識廣的樂評人,也不禁面色刷白。」(萊布雷希特:《誰殺了古典音樂》,頁281-2,上海:世界圖書出版社,2003年)
前述同期《明周》中,劉偉民在《我的音樂選擇》專欄寫道:「對於古典音樂或傳統音樂工作者,『性』似乎仍是一個禁忌。」而《誰殺了古典音樂》(左圖)的英國樂評人萊布雷希特(他在加拿大的Scena網站有定期專欄),更在書中對Vanessa Mae之流大加鞭撻:「這股風潮在陳美的身上達到了低俗的極致...這位小女孩身著貼身內衣,眯眼噘咀地對著攝影機做出老練的表情。對於一個電影女明星來說或許可以接受的行為,出現在應以音樂內涵為努力方向的音樂家,和擁有悠久傳統的唱片公司(按:EMI)身上時,實在教人難以調論。即使是見多識廣的樂評人,也不禁面色刷白。」(萊布雷希特:《誰殺了古典音樂》,頁281-2,上海:世界圖書出版社,2003年)
在日漸萎縮的古典音樂演奏市場中,要闖出一個名堂來的唯一出路,是否就是要採取Vanessa Mae、BOND及Maskim的手法?劉偉民稱讚Vanessa Mae是個「不折不扣的音樂天才」(下略),其他稍有名堂的演奏家又何嘗不是?如十九世紀巴格尼尼(N. Paganini)的小提琴協奏曲,在當時被視為只有作曲家本人才能奏,但是現在從音樂學院畢業的學生們,大部分都能演奏這些難度極高的曲子了。就在水平一致提高,而各人的差別不大的情況下,要「出位」成名,除了贏得國際大賽大獎(不過所謂比賽的數量也太多,真正著名--能平地一聲雷者--則太少)外,相信只有與商業這個「魔鬼」結合,才能提高知名度。
我覺得,要在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中,仍然要「堅持」古典音樂的「純淨」,才是令古典音樂死氣沉沉的主因。以我的情況而言,我在年幼時看不少配了古典音樂樂章的卡通片(主要是美國的),到了開始對古典音樂產生興趣以後,才驚覺不少著名的樂章,已在我小時涉獵過,只是只聽其片面,而非整首而已。若然連一些稍為「破格」、旨在推廣古典音樂的方法,在古典音樂迷中也是離經叛道的話,那末他們實在是食古不化--他們給予古典音樂演奏家的擔子,未免實在太重!(記得數年前陳奕迅的《太空漫遊》一曲,將理察史特勞斯的《查拉斯塔如是說》的著名開首片後不斷重覆,就有人在本港一個古典音樂討論區中肆意抹黑)
但是,最大的問題,仍是這些走商業化、Cross Over路線的「古典音樂藝人」,如何及能否回復「正統」?因為在我的所象中,似乎未有人成功轉型呢。
(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二日下午動筆,十月十三日凌晨三時完成)
 前言:今天(周四)讀《信報》文化版,林在山訪問了剛在今天度過二十二歲生日的李雲迪。此文以李雲迪第一身的角度說音樂,讀來十分有趣,特在此轉貼以與各位對音樂有興趣的人分享。
前言:今天(周四)讀《信報》文化版,林在山訪問了剛在今天度過二十二歲生日的李雲迪。此文以李雲迪第一身的角度說音樂,讀來十分有趣,特在此轉貼以與各位對音樂有興趣的人分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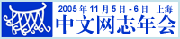
 ONE LONDON, NOT DIVIDED
(from
ONE LONDON, NOT DIVIDED
(from 











